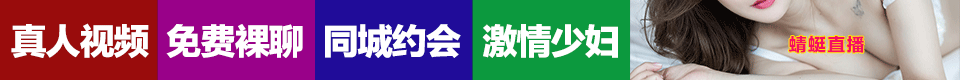手中拿着那一千元不知如何是好,在街上无目的走着。
走了很久,但这也不是办法的,看看报纸找找工作。
「有没有学历证明吗?」老板问
「……」
「那我也没有办法了,你还是走吧!」
她在街上,走着走着,心中混乱,夜色已渐渐的挂上,她到红灯区逛着,看着一盏盏的黄色招牌,鼓起勇气的走上。
「小姐你来做什麽的?」一店中的男人说。
「我……我来做妓女!」她说。
「是吗?」那男的一手扼到她的乳房上去。
「呀!不要!」凌婉说
「你是不想做吗!」男的说,她只好忍想痛楚,低着头。男的更是老实不客气的双手扼到她的双乳去,一口吻到她的唇上。她只是任由他摸着。
「趴下来!」男的说,凌婉照着他所说的做,趴到台上「为什麽不脱衣服,老子怎干你呀!」他说,凌婉只好羞怯怯的把衣服一件不漏的脱光了,雪白的屁股高高的抬起对着他。
「让我干死你吧!」血红的阴茎,一股脑儿的插进去,「呀~~!痛!」乾涸的阴道被插得泪水流出来,男的插得更是起劲,凌婉紧紧的抓着台边,忍着痛楚,屁股被扼到红起来。
「呀~呀~!」身体渐渐适应了,痛楚转化为快感流到全身,呻呤声在嘴边 了出来。
「好一个淫娃!」他说,巨大的肉肠从凌婉的肉体拔了出来,小穴不由的一阵空虚,男的一手抽着她的头发,沾满自已爱液的巨棒插到她的口中,凌婉起劲的含着,舌头就似小蛇般缠绕着那红红的大肉棒。
「吱~吱~」精液射到她的面上去,男的只匆匆的穿回裤子,说:
「还可以吧!以你这样的质素,还可到些大夜总会去做小姐的。」他说。「到最尾的那间房去吧,有客人自然会进来的!」
凌婉走到那房间中,内里的一切也是残残旧旧的,心中不是味儿,虽说从前被人操惯了的,但心中仍是不太好受。脱光衣服,身体不由一股自在的感觉,躺到床上,不一会便沉沉的睡了。
接着一年开始她在这里干着皮肉的生活,钱也储了一点点,到了别一个城市去过着平凡的生活,从前的事她一点也不想去记起,或说是去计较从前的事。在那平静的城市间与一个大她叁年的男人结了婚,那年她是二十岁。
宁静、空洞的房中扬着阵阵的呼吸声,好久方才静下来,空气中扬溢着平和的气纷。
凌婉依偎在明的身体,激烈过后,她仍暗暗的娇喘着,香汗淋漓,累得指头也动不起。
明轻轻的拨着她的发,阵阵的体香在她的身体上散发出来,他从未看过如此完美的身体,手轻扫着那完美无瑕的背。那是一个安宁的星期天,凌婉婚后的叁个月,明是她的丈夫,不知为何,有一次看见他,便深深的爱上了他,於是结识后不足一个月便结了婚。明见凌婉睡着了,静静的起来,为她盖好被,走了出去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「喜欢吗?」冥言说。
「多谢大人,属下很喜欢。」明说。
「不错,这是我们最新的技术,那麽完美的身体我也有点不舍得,你要好好的珍惜,以后通知你才来吧!小心她知道!」冥言说。
「那我走了!」
明回到家中凌婉已急不及待的出来搂着他。
「你去了哪里?怎样也好也对人家说一声!」她说。
「知道了!」明一点也不在意她所说的,只感到她那丰满柔软 乳房压在他的身体上,双手探到她的身后扼着那屁股。
「不要呀!」她说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冥言看着,一大堆资料问道:「怎样?进度如何?」「不!不行!造不回凌婉那个身体」一个技术员说。
「怎会这样的!」
「那次实验其实是一个错误,只是进行到一半便停止。」「那可以再错一次吧!」
「不行!上次这个总部就差一点就完蛋。」
「那就好好研究上一次的失败好了。」冥言说完后走了。
冥言回到自己的房中,一个赤裸裸的少女已坐在床上,羞怯怯的拥被而坐。
走到她的身旁坐着,手轻搭在她那如玉光滑白香肩上,隐隐感到她的身体在抖震着,面上一片嫣红。身体火热的。
「怕吗?」冥言问。少女只是微微的点头,不敢正视着他。
他的手慢慢的从她的肩上滑下来,捉着她那雪白的纤的手指,扼着她的小手。少女缩了一缩,但又停了下来没再一点挣扎,闭上了眼睛,呼吸急促起来。
「算了吧!」冥言突然的站起来,转身便起了。少女只是呆呆看着他的背影的消散。
「伏~」少女翻下,舒适的躺到床上,重重的舒了一口气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这是故事附加的部份。
「呜~呜~」那年凌婉五岁,故事的十六年前。
「为什麽哭呀?婉儿!」她的母亲蹲在地上,轻轻的抚摸着她的头。
「没~没什麽了!」凌婉强忍着泪水,拍拍身上的尘,再一次索着母亲的手,展示着笑容,母亲亦微笑看着她。
十一月,大阳依然的耀眼,母亲性感的扮装拖着可爱 小凌婉在街上走,不一会转入餐厅中,已可看见爸已在内面了。
「爸~!」
「婉儿~乖~!」婉儿喝着那冰凉的红豆冰,不知为可仍是红豆冰,那该是很冷的天气。她欢喜地的吃着,很好味!看着爸妈了很久,但是一点也不懂。
「妈!」凌婉说
「一会我们到游乐场吧!」她说。
「……」
「乒~~~~~」琉璃的碎片满桌也是,爸狠狠的扼着妈妈的颈,好不容易才摆脱,母亲一手索着婉儿的手便走了,头也不回,由始到终也不知是什麽的事。
「妈妈!我们到哪儿呀!我很累呀!」婉儿说。
「是~是吗?」她打开手袋看了一会,心中又不禁好一阵子犹疑着。
「来!跟妈妈来!」走到一公寓中,妈向那位老头说了几句,便走到房中去,坐到床上,轻轻的细抚着凌婉的头发,说着一些不明白的说话,而她的衣服一件件的褪下,最后光脱脱的对着凌婉,紧紧的搂着她。
这是凌婉第一次这麽贴近妈妈的身体,很暖、很软、很滑的身体,这觉感是……是……
「这细路女是送的吗?」一中年的男人走进来道。
「乖!坐到沙发去吧!」妈妈对她。
「她看着没问题吗?」那男的说
「你做就做吧,不用理这麽多!」
男的快手快脚的已把身上的衣脱个清光,妈那双大腿张开,那一黑漆的地方放露着粉红的肉光,她把手指放进口中,口水沾到阴户上,男的那硕大的阴茎插了进去,妈的面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,「啪啪」的响声在两人交接处响着,汗流浃背,妈的口中发出奇怪的叫唤,那痛苦的表情久久不散,吃力的忍受着似的。
妈像小狗般爬到床上,男的依然疯狂的摆动那身体,妈看了凌婉一眼,她笑了,在那痛苦的表情中出现了那笑容,凌婉不由怕起来,紧抓着沙发发抖着。
「伏~」两人倒下,妈的面上沾了不少白色的液体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「嗄!嗄!」妈在床上的喘息声,那男人的身体仍压着她。刹那凌婉看怕了,一个前步往门冲出去,但已是迟了一步,红得发紫的阴茎在她的面前摆动着,她吓怕了想逃但不成,头发已被抓着。
「不要碰我的女儿!」妈拖着疲累的身躯,扑上前抱起凌婉,妈的身体颤抖着。
「二倍,不!叁倍!母女一同来吧!」男的说。
「你!你变态的!」闪身撞到那男人的身上,往门外冲出,突然的停了,定在门处,妈的肩膀已给抓往了,妈的手放开。
「婉儿,走吧!妈待会找你!」婉儿看了妈一眼,走了出去,手挣朝那东西击上去,男的痛得弯下腰来,但妈逃出门外时,重重的一脚已朝那光脱脱的屁股踢上去。
「碰~~~~~~~~~~~!」妈撞到墙上昏过去。
「臭婆娘!操多你多几次也补偿不了!」拖着她再到房中去。
「嘿!看什麽!」一少年在她的身拍了凌婉一下。
「没……没什麽!」她说。
「我叫言,有什麽事找我吧!」婉转身时,那叫言的少年不见了。
她再走到那房间中,什麽都没看见,有着的只有血,全身披着血的妈妈。
血……
「伏~~~~」刹那凌婉醒来了,紧紧搂着那个身躯,很温暖,一个令她很安详的身躯,轻轻的离开他的身体。
「言,为~为什是你的?」凌婉说。
「为何不可?」冥言说,凌婉哭了,真正的哭了,不是怕,不是委屈,可以说什麽也不是,她太快乐了。
「一切也完了!想知吗?」冥言说。
「不!什麽也不想知道?」凌婉说。
【完】